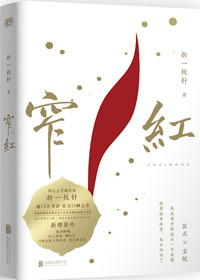
小說–窄紅–窄红
漫畫–想要撒嬌–想要撒娇
段小鈞幫寶綻把斧正架進屋, 到了家,匡正放鬆下,酒牛勁略微方, 胡里胡塗摟着寶綻的腰,說好傢伙也不停止。
“小段, ”寶綻兩難地撥拉他,“困苦你幫我倒杯水, 在雪櫃那裡。”
段小鈞首輪見郢正如此這般粘人, 眼眸都要從眼眶裡掉進去了, 一步三洗心革面地去廚, 涼水壺和組成部分倒置的瓷杯身處小托盤上, 壺裡是再數見不鮮最好的湯。
他端着水回宴會廳, 沙發上沒人了,往樓梯那裡走幾步,在一樓側首的廁所睃部分並坐在網上的人影兒。
匡吐了,抱着恭桶嘔得兇惡, 寶綻鄰近他, 手插進頭髮裡給他揉頭髮屑:“安閒,吐整潔就痛痛快快了。”
他們內有一種空氣, 段小鈞說不好,風和日暖,血肉相連,再有些清晰,像築起了共同看不見的牆, 讓他然的第三者礙手礙腳在。
改正吐了一輪兒, 舒適地放下着腦部,寶綻少許沒嫌他髒, 幫他把洋裝外套脫掉,隔着薄薄一層襯衫,耐性地給他順脯:“痛快點了嗎?”
匡正皺着眉梢看他,洞若觀火沒認出去,兇巴巴地嚷:“你們這時候……怎麼樣供職!”他抓着寶綻的腕子,“我要的酒呢!”
“酒……”寶綻棄暗投明瞧瞧段小鈞,趕早不趕晚招,“酒來了!”
段小鈞這才出來,把水遞給寶綻,看他往匡正嘴邊送:“來,”他怕嗆着他,動彈很慢,“漱濯。”
首席總裁戀上天價前妻
匡千依百順地含着水,漱了漱,陡然咕咚轉瞬,全嚥了。
“哎先祖!”寶綻氣得拍了他一把,在地板磚桌上跪初始,託着他的頦:“這回不許嚥了啊,唯命是從!”
糾正也不分曉哪根筋搭牢了,大概是錯把寶綻算了翡翠日頭的女士,借風使船把人往懷一拽,吸氣,在他口角上親了一口。
轉眼的事,寶綻無意識一揚手,啪地,給了他一嘴巴。
段小鈞親見這一來一往,眨了眨眼,懵了。
寶綻本年二十八,沒和人接到吻,眼下臉面通紅,嫺背大力擦嘴,窘態地躲着段小鈞的視線——被郢正親過的者燙,像要燒着了。
“了不得,寶哥……”段小鈞一看這氛圍,稀鬆再待下來,“人我送到了,那喲,車在前頭等着,我先走了。”
寶綻頭也不擡,悶聲說:“不送你了。”
段小鈞轉身開走,外不脛而走街門聲,寶綻這纔敢看糾正,那東西沒骨類同栽歪在門邊,左臉孔有個煞白的手印。
“哥?”寶綻沒料到自個兒幫手這樣重,快捷把他扶老攜幼來,碰了碰那片發紅的肌膚,“打疼了吧?”
有求必應佛
矯正沒辭令,類似酒還沒醒。
寶綻捋着他亂的頭髮,心疼地說:“你結局爲什麼了?”
“喝……”郢正自言自語,一頭撞在他頸彎裡,熱氣噴着領根,“少贅述,陪我喝……”
“好,”寶綻嘆連續,“我陪你喝!”
他回身去找水杯,更正卻不讓,像是怕他跑了,籠絡上肢把他圈緊,從一下近得不許再近的反差瞄他。
寶綻渾身的牛皮失和都下車伊始了,但沒路人,他也就嬌縱了這個酒徒:“等你明兒酒醒的,”他咕唧,“看我怎收束你!”
“我開心……”改正猛不防呢喃,一改素日的謙讓,有一點荒無人煙的頑強。
寶綻發愣了。
“我哀傷,”指正再次,箍着他的肩膀,“我他媽傷心得要炸了!”
“哥你幹什麼了?”寶綻捧着他的臉,嘴脣和吻的偏離只要幾納米,“你跟我說!”
這就是說近,矯正順其自然把腦門子抵在他的腦門上:“我跟了秩的兄長,”他好好慣了,不服慣了,倘若偏向藉着酒勁兒,基業說不出這些話,“像扔廢棄物同義把我扔了,扔到一下破下身纏腿的場地,讓我自生自滅!”
他說的病很明擺着,寶綻猜是業上出終止,他纔會喝諸如此類多酒,把和睦施行成斯哪堪的花式。
“誰也不許信……”斧正蹭着他的額頭,“此社會,除卻親媽親爸,誰也不行信!”
寶綻立馬抱緊他,平和地拍他的背。
“寶綻……”斧正像是叫他的名字,其實否則,“再有歡唱的寶綻,他決不會騙我,他對我好……”
寶綻轉瞬間睜大雙眸。
“都他媽是壞蛋……”糾正從他額上滑下去,滑到他激烈跳的心坎,“我也是個狗崽子,全是歹徒……”
星空 之 合 漫畫
從一度醉漢班裡聽到然的和氣,寶綻說不養生外頭的體驗,睫毛顫了顫,眼底熱得像有一滴淚要輩出來,他儘先瞠圓雙目,挽起郢政的膀臂:“哥,開班,咱不在這時待着,咱回屋!”
匡正醉得泥維妙維肖,不受他任人擺佈,兩部分你擁着我我蹭着你,翩翩起舞誠如往蜂房挪。屋子寶綻每日都掃,很淨空,鋪墊是備的,他倆夾倒在上頭,漆黑的室,柔嫩的海綿墊彈了彈。
寶綻喘了一陣,爬起來給他脫行頭,襯衣、筒褲、臭襪子,疊好了雄居腳凳上,事後去茅房擰了條熱冪,坐在牀邊,星點擦他身上的汗。
郢政滿意得直哼,一些次抓着寶綻的手,臭羞與爲伍地說醉話:“別吊我興致……你恢復……快點!”
寶綻清晰他說的偏向喲善舉,宜擦到股根,夾着那裡的肉矢志不渝擰了一把,修正啊地叫了一聲,不鬧了。
燮間都疏理截止,寶綻進城把調諧的被子抱下,鋪在匡外緣,他怕他傍晚再吐,嘔吐物如果堵着支氣管,耳邊沒人家塗鴉。
躺下的辰光都三點多了,寶綻趁着指正睡,聽着深深的闊的人工呼吸,慢慢閉着眼。
這一夜很短,一張牀上兩個並列的被窩,被子裡的夢卻很長。匡夢到了友愛的學生期,極度的大學,最讓人羨慕的專科,最完好無損的女友,他是上上下下人胸中的不倒翁。
收受萬融offer那天,他用攢下來的零花錢買了一隻萬寶龍計時碼錶,戴着這隻表,他根本次走進白寅午的辦公,那會兒的老白容光煥發,拍着他的肩頭說:“貨色,跟着我幹,我給你全世界!”
斧正猝醒轉,像是驚悉了真正的夢幻,在十年後的而今,那實物應承過的全國未然渾然一體。
前頭是一派陌生的藻井,宿醉帶輕微的惡意和肌肉痠痛,他逐步伸了個懶腰,一轉頭,對上的是寶綻溫情的臉。
他一動,寶綻也醒了,卷着被子自語:“哥……”
昨日的追念源源而來,白寅午在寫字檯後烤呂宋菸的眼,方襄理錯身而不興的一聲輕哼,代善鬣狗般借刀殺人狡猾的笑容,再有海淀區慌劇團,一張被散失的舊像片,硬玉太陽的狂歡,和狂歡之後迎他回家的寶綻。
這瞬時,改正寸心時有發生一股烈性的民族情,他光榮在以此蹭蹬的早上,寶綻能陪在他潭邊,坐這個人的設有,他不須在更衣室的地板上甦醒,毫無着被嘔吐物污穢的襯衫,偌大的獨棟別墅,他毫不一度人吞食職臺上難言的苦痛。
獨來獨往的生存,他早已過夠了。
“哥,”寶綻眯察睛不啓,“首疼嗎?”
“還行,”匡也沒起,和他臉對着臉裹在被窩裡,“我把你下手甚吧?”
“嗯,”寶綻點點頭,“你可太令人作嘔了。”
匡正聽他這樣說,卻笑了,笑得很夷愉,打開被子往隨身瞧:“喲,你伢兒給我扒的夠淨空的。”
寶綻半邊臉壓在枕頭上,像是嘟着嘴:“你覺着我歡喜啊,臭襪子可臭了。”
靈動的 小說 窄红 47.四七 探索
2025年2月6日
未分类
No Comments
Strawberry, Rory
小說–窄紅–窄红
漫畫–想要撒嬌–想要撒娇
段小鈞幫寶綻把斧正架進屋, 到了家,匡正放鬆下,酒牛勁略微方, 胡里胡塗摟着寶綻的腰,說好傢伙也不停止。
“小段, ”寶綻兩難地撥拉他,“困苦你幫我倒杯水, 在雪櫃那裡。”
段小鈞首輪見郢正如此這般粘人, 眼眸都要從眼眶裡掉進去了, 一步三洗心革面地去廚, 涼水壺和組成部分倒置的瓷杯身處小托盤上, 壺裡是再數見不鮮最好的湯。
他端着水回宴會廳, 沙發上沒人了,往樓梯那裡走幾步,在一樓側首的廁所睃部分並坐在網上的人影兒。
匡吐了,抱着恭桶嘔得兇惡, 寶綻鄰近他, 手插進頭髮裡給他揉頭髮屑:“安閒,吐整潔就痛痛快快了。”
他們內有一種空氣, 段小鈞說不好,風和日暖,血肉相連,再有些清晰,像築起了共同看不見的牆, 讓他然的第三者礙手礙腳在。
改正吐了一輪兒, 舒適地放下着腦部,寶綻少許沒嫌他髒, 幫他把洋裝外套脫掉,隔着薄薄一層襯衫,耐性地給他順脯:“痛快點了嗎?”
匡正皺着眉梢看他,洞若觀火沒認出去,兇巴巴地嚷:“你們這時候……怎麼樣供職!”他抓着寶綻的腕子,“我要的酒呢!”
“酒……”寶綻棄暗投明瞧瞧段小鈞,趕早不趕晚招,“酒來了!”
段小鈞這才出來,把水遞給寶綻,看他往匡正嘴邊送:“來,”他怕嗆着他,動彈很慢,“漱濯。”
首席總裁戀上天價前妻
匡千依百順地含着水,漱了漱,陡然咕咚轉瞬,全嚥了。
“哎先祖!”寶綻氣得拍了他一把,在地板磚桌上跪初始,託着他的頦:“這回不許嚥了啊,唯命是從!”
糾正也不分曉哪根筋搭牢了,大概是錯把寶綻算了翡翠日頭的女士,借風使船把人往懷一拽,吸氣,在他口角上親了一口。
轉眼的事,寶綻無意識一揚手,啪地,給了他一嘴巴。
段小鈞親見這一來一往,眨了眨眼,懵了。
寶綻本年二十八,沒和人接到吻,眼下臉面通紅,嫺背大力擦嘴,窘態地躲着段小鈞的視線——被郢正親過的者燙,像要燒着了。
“了不得,寶哥……”段小鈞一看這氛圍,稀鬆再待下來,“人我送到了,那喲,車在前頭等着,我先走了。”
寶綻頭也不擡,悶聲說:“不送你了。”
段小鈞轉身開走,外不脛而走街門聲,寶綻這纔敢看糾正,那東西沒骨類同栽歪在門邊,左臉孔有個煞白的手印。
“哥?”寶綻沒料到自個兒幫手這樣重,快捷把他扶老攜幼來,碰了碰那片發紅的肌膚,“打疼了吧?”
有求必應佛
矯正沒辭令,類似酒還沒醒。
寶綻捋着他亂的頭髮,心疼地說:“你結局爲什麼了?”
“喝……”郢正自言自語,一頭撞在他頸彎裡,熱氣噴着領根,“少贅述,陪我喝……”
“好,”寶綻嘆連續,“我陪你喝!”
他回身去找水杯,更正卻不讓,像是怕他跑了,籠絡上肢把他圈緊,從一下近得不許再近的反差瞄他。
寶綻渾身的牛皮失和都下車伊始了,但沒路人,他也就嬌縱了這個酒徒:“等你明兒酒醒的,”他咕唧,“看我怎收束你!”
“我開心……”改正猛不防呢喃,一改素日的謙讓,有一點荒無人煙的頑強。
寶綻發愣了。
“我哀傷,”指正再次,箍着他的肩膀,“我他媽傷心得要炸了!”
“哥你幹什麼了?”寶綻捧着他的臉,嘴脣和吻的偏離只要幾納米,“你跟我說!”
這就是說近,矯正順其自然把腦門子抵在他的腦門上:“我跟了秩的兄長,”他好好慣了,不服慣了,倘若偏向藉着酒勁兒,基業說不出這些話,“像扔廢棄物同義把我扔了,扔到一下破下身纏腿的場地,讓我自生自滅!”
他說的病很明擺着,寶綻猜是業上出終止,他纔會喝諸如此類多酒,把和睦施行成斯哪堪的花式。
“誰也不許信……”斧正蹭着他的額頭,“此社會,除卻親媽親爸,誰也不行信!”
寶綻立馬抱緊他,平和地拍他的背。
“寶綻……”斧正像是叫他的名字,其實否則,“再有歡唱的寶綻,他決不會騙我,他對我好……”
寶綻轉瞬間睜大雙眸。
“都他媽是壞蛋……”糾正從他額上滑下去,滑到他激烈跳的心坎,“我也是個狗崽子,全是歹徒……”
星空 之 合 漫畫
從一度醉漢班裡聽到然的和氣,寶綻說不養生外頭的體驗,睫毛顫了顫,眼底熱得像有一滴淚要輩出來,他儘先瞠圓雙目,挽起郢政的膀臂:“哥,開班,咱不在這時待着,咱回屋!”
匡正醉得泥維妙維肖,不受他任人擺佈,兩部分你擁着我我蹭着你,翩翩起舞誠如往蜂房挪。屋子寶綻每日都掃,很淨空,鋪墊是備的,他倆夾倒在上頭,漆黑的室,柔嫩的海綿墊彈了彈。
寶綻喘了一陣,爬起來給他脫行頭,襯衣、筒褲、臭襪子,疊好了雄居腳凳上,事後去茅房擰了條熱冪,坐在牀邊,星點擦他身上的汗。
郢政滿意得直哼,一些次抓着寶綻的手,臭羞與爲伍地說醉話:“別吊我興致……你恢復……快點!”
寶綻清晰他說的偏向喲善舉,宜擦到股根,夾着那裡的肉矢志不渝擰了一把,修正啊地叫了一聲,不鬧了。
燮間都疏理截止,寶綻進城把調諧的被子抱下,鋪在匡外緣,他怕他傍晚再吐,嘔吐物如果堵着支氣管,耳邊沒人家塗鴉。
躺下的辰光都三點多了,寶綻趁着指正睡,聽着深深的闊的人工呼吸,慢慢閉着眼。
這一夜很短,一張牀上兩個並列的被窩,被子裡的夢卻很長。匡夢到了友愛的學生期,極度的大學,最讓人羨慕的專科,最完好無損的女友,他是上上下下人胸中的不倒翁。
收受萬融offer那天,他用攢下來的零花錢買了一隻萬寶龍計時碼錶,戴着這隻表,他根本次走進白寅午的辦公,那會兒的老白容光煥發,拍着他的肩頭說:“貨色,跟着我幹,我給你全世界!”
斧正猝醒轉,像是驚悉了真正的夢幻,在十年後的而今,那實物應承過的全國未然渾然一體。
前頭是一派陌生的藻井,宿醉帶輕微的惡意和肌肉痠痛,他逐步伸了個懶腰,一轉頭,對上的是寶綻溫情的臉。
他一動,寶綻也醒了,卷着被子自語:“哥……”
昨日的追念源源而來,白寅午在寫字檯後烤呂宋菸的眼,方襄理錯身而不興的一聲輕哼,代善鬣狗般借刀殺人狡猾的笑容,再有海淀區慌劇團,一張被散失的舊像片,硬玉太陽的狂歡,和狂歡之後迎他回家的寶綻。
這瞬時,改正寸心時有發生一股烈性的民族情,他光榮在以此蹭蹬的早上,寶綻能陪在他潭邊,坐這個人的設有,他不須在更衣室的地板上甦醒,毫無着被嘔吐物污穢的襯衫,偌大的獨棟別墅,他毫不一度人吞食職臺上難言的苦痛。
獨來獨往的生存,他早已過夠了。
“哥,”寶綻眯察睛不啓,“首疼嗎?”
“還行,”匡也沒起,和他臉對着臉裹在被窩裡,“我把你下手甚吧?”
“嗯,”寶綻點點頭,“你可太令人作嘔了。”
匡正聽他這樣說,卻笑了,笑得很夷愉,打開被子往隨身瞧:“喲,你伢兒給我扒的夠淨空的。”
寶綻半邊臉壓在枕頭上,像是嘟着嘴:“你覺着我歡喜啊,臭襪子可臭了。”